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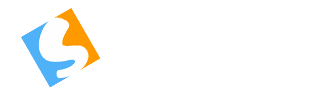
本期金句:“艺术的好坏,从来跟长短无关,只跟态度有关”
01 “我的班,只教有基础的演员”
“我是不教素人的。”郝蕾这句话说得很干脆。
在她位于北京的表演训练教室里,过去一年半已经办了三季课程,2025年冬季班刚刚结束面试。从近六百名报名者中筛选出九十多人面试,最终只留下二十余人。这样的淘汰率,堪比顶尖艺术院校的招生。

“如果一个夏季班或冬季班只有十几天,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帮助。”郝蕾解释着她的招生标准,“我们要么要求本科或研究生是表演专业,要么要求履历上有丰富的实战经验。”
这样的门槛,初听有些“不接地气”,但了解她的教学方式后,你会明白其中的必要性。
郝蕾的教学理念源于二十年前她了解到的“纽约演员讲习所”——那是马龙·白兰度和索菲亚·罗兰创办的分享式课堂,不是刻板的书本教学,而是将经验融合成实战方法。
“我听完后就决定,有朝一日也要做这件事。”

02 从“犀利导师”到“温暖师者”:被误解的郝蕾
在表演类综艺中,郝蕾常以“犀利”形象出现。她的点评直接,不留情面,这让很多人认为她骨子里存在“鄙视链”——看不起流量演员,看不上微短剧。
“这完全是个误解。”郝蕾笑着对采访者谭飞说。
她提到最近面试的一位女演员,对方因出演爆火微短剧而广为人知。“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她,停下来是因为她演得不像其他短剧那样浮夸。”面试时,郝蕾特意问了她的拍摄感受,发现剧组专业度不亚于长剧团队。

“短剧怎么了?短剧难道不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下来的吗?”郝蕾反问道,“艺术的好坏怎么会跟长短有关系?重要的是创作态度。”
对于流量偶像,她同样表现出理解:“偶像是另一个行当,他们在扮演‘偶像’这个角色。如果他们想转型做演员,我欢迎,但不能假模假式地说‘因为我红,所以我会演戏’。”
在郝蕾的课堂上,学员要经历的是“残酷的真实”。
“我的课堂是非常残酷的。”郝蕾直言,“你要分分钟被剥开,做情绪的过山车。”
她反对传统表演教学一上来就做“无实物表演”或“动物模拟”:“那会封锁孩子的天性。他们觉得掌握了那些技巧就能入行,但其实走不长。”
什么是好的表演?郝蕾的答案很明确:“不像演的。”
她以张颂文为例:“他演的高启强是张颂文吗?肯定不是。好演员都是把角色‘化’在自己身上。”
但这种能力如何培养?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学校毕业、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演员?
“谁说张颂文演过贪官、做过黑社会?”郝蕾笑道,“演员的取材永远有限,关键是如何调动自己的感知。我们一起经历同一件事,感受可能完全相反。演员的工作本质是孤独的。”

聊到行业现状时,郝蕾的语气明显沉重起来。
“大家只看到金字塔顶的光鲜,不知道底下有多少演员月入两三千,没有五险一金。”
她讲述了一个令她落泪的故事:赖声川话剧《曾经如是》中的一位年轻演员,在疫情期间白天演出,晚上送外卖,演到晚上十点后再去送单到凌晨两三点。

“这样的好孩子,如此热爱表演,我们为什么不能想办法帮助他?”
这也是她坚持开班授课的原因之一。她的教师团队中有很多戏剧演员,“我希望他们除了等待演出的时间外,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,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”
03 “松弛感”是最贵的奢侈品
在表演行业,“松弛感”成了稀缺品。
郝蕾刚参加完乌镇戏剧节,观摩了开幕大戏:“十八个演员的松弛程度让我震惊。我一边看一边检讨自己,演戏剧时我总是不够松弛。”
如何培养松弛感?她的答案出人意料:“尊重天性是解放天性的前提。”
“如果一个人天生害羞,我们要承认这份害羞。梁朝伟还社恐呢。”郝蕾说,“关键是看到真实的自己,并相信这种真实有魅力。”
她的课堂反馈中最让她欣慰的是,学员常说:“老师,做自己好爽。”
但这种觉醒并不容易。“生活永远是艺术的前提。”郝蕾感慨,“老师用尽方法帮你打开心门,生活的一记重拳就能把它关上。”
她提到纪凌尘:“去年夏天他是优秀毕业生,但后来‘还给老师了’。我能理解,生活的困难远超课堂上的表演练习。”
04 给青年人的话:在流量时代守住表演的尊严
面对当下“数据至上”的行业环境,郝蕾表现出难得的宽容。
“这不是某个孩子的错。制作方、平台、观众都要看数据,没有数据就没有工作机会。让一个人保持初心,太艰难了。”
但她相信会“触底反弹”:“一定会有部分孩子找到解决困境的方法。这是他们的时代,他们有他们的痛苦。”
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,郝蕾坦言近年自己变得更有同理心:“我必须换位思考,否则无法与孩子交流。这种变化也让我更能理解年轻演员。”
对于青年创作者,她的建议是:“传统需要被尊重。电影有历史,表演有历史,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。但不必急于说教,让孩子们先去经历,叛逆完了,他们会发现人类文明发展逃不出某些规律。”
采访最后,郝蕾罕见地谈起自己刚来北京时的日子。
十六七岁的她住在半地下室,整栋楼几乎没人,“那是相当恐怖的经历,那种孤独感的阴影存在了好多年。”
她做配音养活自己,冬天骑着自行车从五棵松到儿影厂,多少次因路滑摔倒。“那时候出租车十块钱,我不舍得打,除非和人拼车出三五块。”

“谁都过过苦日子,只是大家只看到你闪耀的一面。”
或许正是这些经历,让今天的郝蕾在保持专业挑剔的同时,对每一个坚持表演的人心存悲悯。
她的表演班学费不高,“孩子们放下手头不多的工作来学习,我不给他们真东西,是最大的不负责。”

窗外天色已晚,郝蕾还要准备明天的课程。在这个流量更迭比翻书还快的时代,她依然坚信:真正的表演,是能够穿越时间的东西。
而她的课堂,正试图为这个行业留住这种“穿越时间”的能力——一个演员,一个演员地教,一场戏,一场戏地磨。
这是一条公告